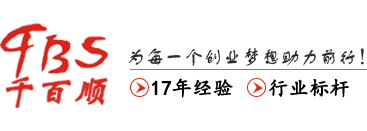陳侶白與有關出版者“臺灣高山族民歌”署名權的糾紛案
更新時間:2020-12-01 15:41:27
案例概述
上海某出版社委托福建省某文化局編輯《臺灣民歌選》,由陳侶白負責編輯歌詞。臺灣高山族有民族語言而無民族文字。高山族民歌一部分是有詞意,可以譯成漢族文字的,另一部分只有發音而無詞意,只表達一種情緒,必須根據它所表達的情緒來填詞。為了編好這本書,陳侶白等請了十幾位高山族歌手會集福州演唱高山族民歌,加以錄音、記譜,并組織歌詞作家譯詞、填詞。后來上海某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臺灣民歌選》,收入158首歌曲,由陳侶白譯詞、填詞的歌曲較多。《臺灣民歌選》的署名按慣例,在歌譜題目右邊標上流行地區和族名,在歌譜末尾右邊標上演唱者、記譜者、譯詞者或填詞者的姓名。
后來轉載這些歌曲的書刊都照此署名。轉載的大多數書刊都署了陳侶白等填詞者、譯詞者的姓名,但也有部分歌集、盒帶的出版者在轉載時只標“臺灣高山族民歌”而未署填詞者、譯詞者的姓名。陳侶白就此向有關部門申訴,要求有關出版者予以補正。
案例評析
本案涉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整理者的著作權保護問題。高山族民歌屬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范疇,陳侶白等人將無文字的高山族民歌加以翻譯,并用漢字固定下來,屬于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整理,所形成的作品不同于原來傳唱的民歌,原民歌的版權所有者與整理作品的版權所有者不同。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規定:
“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
可見,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只要不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改編者、翻譯者、注釋者和整理者都是著作權主體。
演繹作品是指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演繹作品的獨創性在于它一方面對原作品進行了改編、翻譯、注釋和整理;另一方面又在原作品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對原作品做了形式上的變動。因此,演繹作品與原作品一樣,都是獨立的受保護的作品。演繹作品的作者可以憑借他在演繹原作品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創造性勞動而對演繹作品享有獨立的著作權。著作權法在承認演繹作品的作者享有獨立的著作權的同時,又規定對演繹作品的保護不得損害原作者的權利。第三人在使用演繹作品時,應征求原作者與演繹作品作者的同意。陳侶白等人對高山族民歌翻譯、填詞,對《臺灣民歌選》這一高山族民間文學的整理本享有著作權,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時采用的署名方式,即以適當方式標明歌曲所屬民族和流行地區,演唱者、記譜者、譯詞或填詞者的姓名的署名方式是正確的。
他人有權根據傳唱的民歌,整理、出版自己的民歌選,但陳侶白等人的《臺灣民歌選》出版后,許多書刊按原文轉載,而不是自己重新整理。這種轉載,未征得陳侶白等著作權人的許可,也未向他們支付報酬,并且未署陳侶白等整理者姓名,因而侵犯了陳侶白等人的署名權、獲得報酬權。
侵權的書刊、錄音帶發行者應承擔責任。《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七節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罪,其中第二百一十七條和第二百一十八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刑罰。
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
“以營利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權情形之一,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作品、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
(三)未經錄音錄像制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制作的錄音錄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
第二百一十八條規定:
“以營利為目的,銷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的侵權復制品,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一十七條所列侵犯著作權行為之一,個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具體界限為2萬元以上;單位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具體界限為10萬元以上。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是指下列3種情況:
(1)因侵犯著作權曾經兩次被追究行政責任或者民事責任,又侵犯著作權的;
(2)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10萬元以上,單位非法經營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
(3)造成其他嚴重后果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
?